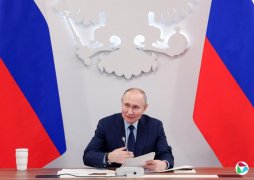如果我们不拓宽对成功的定义,超越自身的相互比较,那么无论如何改变小学离校考试的评分制度,都无法减少学生压力。如果家长把教育部减少的东西加到学生身上,那么取消年中考试也不会减轻学生压力。
今年,我们迎来了新加坡独立60周年、教育部成立70周年,以及国立教育学院成立75周年。值此之际,回顾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展望未来教育的走向,正当其时。
第一阶段——奠基:从分散到统一
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生存就能得到保障。对于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和生存而言,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坚信,我们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教育体系,以实现三个目标:确保国人具备就业技能、建立新生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以及在一触即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中促进社会凝聚力。
建国初期,他们面临三大紧迫而巨大的挑战。
首先,随着人口增长,教育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的威胁。学校严重短缺,许多在战争中受损或被毁,教师也供不应求。
其次,教育体系沿语言断层线划分,各语言源流学校有各自的课程和考试要求。若不采取干预措施,我们可能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不同公民群体,他们只能与使用自己语言的人交流。另一方面,新的工作岗位也越来越需要求职者掌握英语。
第三,教育体系支离破碎。学校由各种组织开办,质量参差不齐。
到1970年代,我们克服了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工业化也创造了许多高薪工作。
但是,随着学校开始招收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语言断层线和教育质量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全球竞争也在加剧。为了确保长期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朝更多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产业发展。这意味着新加坡工人的技能水平必须显著提升。
第二阶段——进步:从潜力到表现
在此背景下,1979年,时任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率领一个团队编写了一份开创性的报告书,为新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报告书认为,对教育体系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已不再适用。如果我们希望充分挖掘多元化人口的全部潜力,就必须照顾到有不同需求、优势和能力的学生。
《吴庆瑞报告书》中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分流制度,即根据学生的语言和学术能力,将他们编入不同课程,使学校能够针对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教学,并营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充分发挥潜力的环境。
为了进一步支持学习能力各异的学生,我们采取其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推出高才教育计划和学习支援计划,以及成立工艺教育学院。
配合这些雄心勃勃的改革,我们必须同时做出努力,进一步支持教育工作者。1973年,师资训练学院改组为教育学院,即国立教育学院的前身。
第三阶段——新路径:从学术走向全面发展
到1990年代末,这些举措已见成效,我们的学生在各种国际测试和平台上表现出色。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世界日新月异,并重塑我们对教育和工作的认知。谁能更快地创新,谁就能领先。
1997年推出的“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民”(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改革,标志着新加坡教育体系进入第三阶段。由时任教育部长张志贤领导,我们为学术能力不一的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教学,使学习更加多样化和丰富。
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学生对事实内容的掌握,而是加强他们提炼和辨别信息的能力。我们制定了支持更全面课程的新政策框架,精简了国家课程,并于1997年制定了第一个资讯科技教育总蓝图。
我们也开始在教育体系中开辟更加开放多元的升学途径,推出不同的课程和学校类型,包括直通车计划,以及新加坡体育学校和云锦中学等专门学校,以满足具备不同能力和抱负的学生的需求。
在采取这些重要举措的同时,我们也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赋予教育工作者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教育工作者的薪资变得更具竞争力。2001年,我们推出全球首创的三轨制教师职业发展体系:“行政领导发展路线”(Leadership Track)、“专科发展路线”(Specialist Track)、“专业教师发展路线”(Teaching Track)。它意味着教师是一个多层面、充满机遇的事业,都可达致卓越巅峰。学校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需求,灵活地调配资源。
近年来,我们继续加强全人教育和多元化发展路径。2023年推出的加强版“21世纪技能”(Enhanced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更加重视适应性和创造性思维、沟通能力和公民素养。2021年,小学离校考试的T值总积分(T-score)制度被积分等级制度取代。就在去年,我们落实全面科目编班计划,取代旧的分流制度。我们正在检讨高才教育计划和直接收生计划。此外,政府和社区资助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我们通过加强学前教育基础和终身学习,以生命周期的方式投资教育。由教育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联合管理的幼儿培育署于2013年成立,负责监管学前教育领域。“技能创前程“”计划于2015年推出,这是全国首个推广终身学习的项目,使我们有别于其他传统上只注重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国家。
未来的方向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水平教育基础所带来的机遇,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首先,社交媒体的普及打开了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回音室效应和错误信息的潘朵拉盒子,这有可能造成社会两极分化。除了能够提炼信息,学会辨别真相、质量和相关性变得更加重要。
其次,人工智能如今已触手可及。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项技术,将能发挥超出自身实力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就会被时代抛在后面。
第三,全球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作为一个小型城市国家,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在世界各地拓展和建立伙伴关系。
我们既不能自满,又不能给学生太大的压力。
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进行的测试,衡量的是当今有价值的能力,但却无法衡量未来所需的新兴技能。
即使我们努力帮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也必须避免过于注重分数,以及在学校实行溫室强化式的拔苗助长(hothousing),因为这会扼杀他们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热爱。
我们也必须摆脱对自身的相互比较的关注。真正的考验不是学生在学校的前15年里是否能超越彼此,而是他们在接下来的50年里是否能不断超越自我。
先辈已把接力棒传给了我们。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必须放眼未来,并思考未来将对我们提出怎样的要求。
我们将进行两项已酝酿多年的结构性调整。
首先,我们会继续支持更大程度的定制教育,以满足学生不同的能力、需求、兴趣和抱负。
其次,社会整体必须拥抱学校和书本之外的学习。教育体系必须抵制过度提供、过度保护和过度结构化的冲动。我们的世界不应局限于学校,相反,世界应成为我们的学校。我们也必须继续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
这些调整必须辅之以持续提升和支持教师队伍的努力,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更复杂的要求。教学从来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
即便我们进行结构性调整,双语政策仍必须是我们教育体系的基石。
持续成功的反思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非从零开始。对于如何持续取得成功,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我们必须在维持开放、持续,以及具有同理心的唯才是用制度的同时,保持对卓越的追求。
我们不能满足于“足够好”。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我们必须把结合实际情况追求卓越,同脱离实际情况追求完美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必须把正确的事情做好,而不仅仅是把同样的事情做好。
在通过唯才是用制度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自身演变成特权的“继承制度”。政策也须不断更新,以在确保社会流动性和维护凝聚力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教育政策中提倡包容和促进融合。
第二,时机是最关键的。我们须具备敏锐的直觉,知道何时须坚定信念,引领大家前行;什么时候又应该运用智慧,根据社会转变的步伐,调整执行政策的速度。人们的思维和社会文化必须与制度变革同步发展,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拓宽对成功的定义,超越自身的相互比较,那么无论如何改变小学离校考试的评分制度,都无法减少学生的压力,也无法让学生的多元才艺受到肯定。如果家长把教育部减少的东西加到学生身上,那么取消年中考试也不会减轻学生压力。
所有政策都会有取舍,尤其是在短期内。政策的连贯性,以及在每代人致力落实政策,也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信念,为国人做正确的事,即使它不受欢迎或令人难以接受。
第三,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更强大。教育部总部、专业机构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须维持团结。
“好老师只去好学校”的情况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发生。我们也不能让政策制定者和在学校前线执行政策的教育工作者之间出现分歧。
我们必须继续在教育体系中培养相互信任,并促进人员、想法和最佳实践的流动。这将确保我们不会变得僵化,避免各自为政,并在提升时共同进步。
第四,社会对教育工作者的尊重程度,决定了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而这反过来又塑造了教育体系的质量。
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以人为本的事业。它引导人民,培养价值观、生活技能、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因此,再多的资金或技术,都无法取代教育工作者所提供的指导和个人联系。
我们对教育工作者的态度和行为,将决定未来加入教育下一代的教师队伍的素质。
最后,学生始终是教育体系的核心。
当我看着学生们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灿烂而期盼的面孔时,我看到了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仍然存在的挑战和未来的工作。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需求接受教育;培养他们坚强的品格;并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实现抱负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须要做的工作。
60年来,新加坡克服重重困难,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繁荣昌盛。这得益于建国元勋的引领,他们即使没有共同的过去,也憧憬着共同的未来。他们团结在唯才是用、廉洁奉公、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理想之下,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对这座岛屿及其人民的承诺。
我们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不仅要协助每个学生发挥最大潜力,还要激发他们为新加坡做出贡献的使命感,以及不畏艰难、继续前进的勇气。
我们虽已做了很多,但这事关我们的未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本文是教育部长于本月11日在由教育部、国立教育学院,以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联办的“从基础发展至前沿——我们的教育之路”讲座上的浓缩版演讲词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