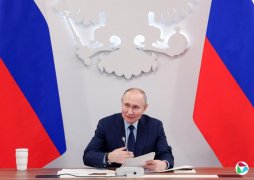来临大选将决定这个新阶段的面貌,它关乎新总理在国内外的威信,还有国家朝野格局是否会迎来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关键转捩点。
2025财政年预算案星期二(2月18日)终于出炉了。这个“选前预算案”果然不负众望,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曾对此有个经典调侃:“政府给你一个鸡腿,之后会跟你要回一整只鸡。”不过,抛开这个“先甜后苦”比喻背后的政治意涵,政府大选前总是手头特别宽裕,其实有行政上的必然性。因为新加坡的宪法规定,每任政府都只能花自己赚来的钱,不能坐享上一任政府所累积的财政盈余,因此这些盈余在政府任满后就必须上缴国库,纳入储备金,而大选后新一任政府组成时,财政上必定由零开始。这也是为什么新任政府往往会先审慎理财,想方设法扩充收入,积极存钱,到了执政中期,才开始有收成能分派。
当然,政府理财有道,积累盈余,如今能够更慷慨解囊,与民共享,全民都乐见,也不太可能有人收到购物券、补贴和回扣等会不开心的。只是,这样的开心就足以达到执政党最希望看到的民意基础向好、形势有利局面吗?答案看来也不会这么简单。
来临选举是黄循财总理接过领导棒子后,正式领军的第一场全国大选。前两任总理吴作栋和李显龙接班后的首场大选,其实都“出师不利”,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都比上一届大选低。吴作栋领军的1991年大选,得票率为61.0%,李显龙带队的2001年大选,得票率则是66.6%。因此,以上届61.24%作为参照,坊间已有执政党的本届大选得票率可能下降的说法。
另外,今年适逢SG60,借鉴2015年SG50时行动党的得票率反弹回近70%,有一种揣测是在喜庆氛围下,国人回顾来时路,感念国家的发展和成功,更倾向于对执政党投支持票。但别忘了2015年毕竟还有一个无法复制的关键事件,就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逝世。这份对前人毕生奉献给新加坡的感恩情绪,对选票造成的直接影响,相信才是决定因素。因此,这回单单纪念建国60年,就未必能为白衣人催出更多支持票。
再者,世界在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如果说危机当前,大环境的不明朗有可能让选民为求稳,普遍投票更保守,2020年在冠病疫情笼罩下举行的大选结果,已颠覆这一传统认知。行动党当时的得票率不只骤减8.66个百分点,成为国家独立后的第三低,还丢失多一个集选区。况且,2024年作为世界选举年,在环球经济挑战面前,也成为世界许多执政党相继败选或失势的一年,行动党政府纵使推出许多措施抗通胀、为民纾困,但要在这股反风中完全不受波及,恐怕也不是易事。
还有,来届大选也迎来约15万名在2000年代诞生的Z世代首投族。这一群体常被形容为由价值观驱动,相对不那么重视物质财富。换句话说,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生活费、就业等民生问题,未必会是左右这群首投族选票走向的主导因素。90后、95后、2000后相继成为合格选民,这些年轻一代距离那段建国艰辛岁月也越来越远,即便能想象却肯定无法如他们父母、祖父母辈般感同身受,因此“成功来之不易”“如今的安逸并非坚不可摧”“失去了很可能再也回不去”,以及“如今的成就归功于行动党政府多年来的治国有道”——这些新加坡领导人不断重复的论述,年轻一代与首投族也不一定买账。对他们来说,眼前所见的是:很多国家更换政府后,无论结果好坏,国家依然能够继续运行;行动党固然说得对、做得对,但国会更多反对党代表有鞭策与制衡作用,再说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一定不行?
基于这种种变数,黄总理从接棒前到就任总理后,已不止一次提到,他不会假定行动党一定会赢得执政权、他理所当然会担任总理。对白衣人来说,最可怕的情况相信不是哪里做得不够或什么做错,而是即便该做的都做到了,还是难抵挡民心思变。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设下的中期目标,是赢得三分之一的议席,以本届政府的93个议席来说,就是工人党在原有的10个议席基础上,再争取拿下多21席。即便这三分之一江山不是蓝衣人一党占据,只要反对党阵营联合夺得,都将史无前例削弱执政党的势力。
黄总理发表财政预算案声明时,形容新加坡来到一甲子,象征一个完整循环,并迈入建国的下一个新阶段。新里程碑不免引发省思:是延续我们所熟悉的,还是求变涉足未知?
来临大选将决定这个新阶段的面貌,它关乎新总理在国内外的威信,还有国家朝野格局是否会迎来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关键转捩点。
对我们这些选民来说,这次大选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要把新加坡的新阶段托付给谁?大选或许每五年一次,但从内到外的事态发展都在预示,选举结果的影响将是深刻亦深远的。
每每来到选举,当前的民生问题总是最牵动民心,但在这一刻,我们更应该以超越个人得失、喜恶与顺逆的大局观,慎重思考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这一票须要对得起国家和子孙后代的未来,而到时什么才是对他们最甜美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